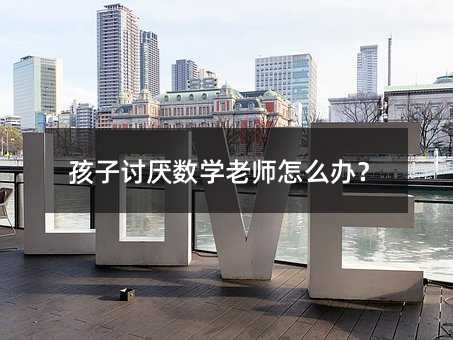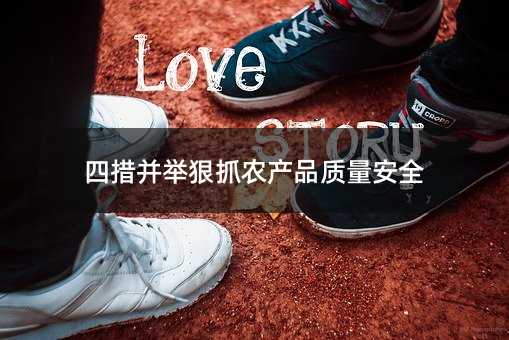国学教育如何会作孽?
换汤不换药就会作孽。
目前不少做国学教育的学校,所做的事情不外乎更换了学习内容,也就是把课本换成了中国古时候的经典、蒙学、诗词,把活动换成了中国古时候的民俗、技艺、非遗,但教育方法没变,教学组织没变,教育理念也没变。仍然是原来的班级,原来的课堂,原来的老师以原来的方法上着原来的课,最后以原来的考试排出原来的名次。
国学教育,不是如此教的。
让大家回到起点。——大家为何要做国学教育?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一上台,立即废除中国传统教育体制,引进西方教育,到目前一百年了。但,西方的体制教育,,即除去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等以外的主体教育,事实上是两条线——school(学校)和church(教堂)。学生是平时去学校,周末去教堂的。学校负责常识和技能的教育,教堂负责理想和信仰的教育。直至今依旧这样。蔡部长只引进了一条线——学校,没引进宗教教育。但如此是不完整的教育呀,蔡部长也了解,于是他在1917年发表了著名的倡导——“以美育代宗教”。然而,今天大家看一看,从国内到台湾,代替了宗教的美育在哪儿?这条线彻底失败。百年中国教育事实上是瘸腿教育。大家缺少理想和信仰的教育。由此,大家的西式学校教育,也永远是“山寨版”,永远差一步,永远有赝品的感觉,如何都办不到位,由于西方的学校教育是以宗教教育为基础的。
这二十多年来的“国学热”,正是感受了切肤之痛的父母发起的。很不容易走至今,是多少同道同仁们艰苦工作的成就。现在希望乍现,大伙摩拳擦掌,切不可忘记了大家的初衷——国学教育,是精神教育,不是常识和技能的教育。今天之所以要做国学教育,是为了弥补那条瘸腿,不是仅仅为了传承中华传统常识和技艺。
要补上中国教育瘸了的这条腿,如何解决?看着中国人仍然是不可能同意宗教教育,所以大家的道路只能是回归传统——像古时候教育那样,把精神教育和常识教育结合在一块进行,也就是放在学校里,由老师进行。目前教育部所做的种种改革尝试,都是指向这个方向。无疑这是对的。
但,大家的学校已经习惯了做常识和技能的教育,他们比较容易就把国学又做成了常识和技能的教育,从而让教育部的好心变成驴肝肺。不只这样,还做出一套新的国学应试教育,把中华传统文化做成中华传统野蛮。
那样,如何才能防止悲剧上演?我相信这不是其他人的初衷。我想,第一就是要牢记国学教育的地位——精神教育、生活态度教育、品性爱文化,第二,就是要了解一个道理:体系决定性质。
到底做的是中国文化教育,还是西方文化教育,这件事并不取决于教育的内容,而是取决于整个的教育体系的性质。
大家的教育一直在用(常常是扭曲化用)中国文化的材料,进行西方文化的教育。所以内容并不可以决定性质。
举例来讲,语文,这门课的名字前面其实省略了一个“汉”字,教的应该是“汉语文”,然而用的是西方语言学理论和西方文学理论,无视中国几千年的声训学术传统,不承认汉字的音形义一体关系,无视汉诗文都是吟诵的事实,不承认声音的涵义,把诗歌讲成poety,小说讲成novel,枯燥乏味,无情无理!
再举例说,历史,这门课事实上是中国history,讲的都是一个朝代是如何开始如何灭亡的,获得了什么收获,进步了什么经济和文化。可是,大家的二十四史,是传记体的,讲的是人的故事,人性的历史。这才叫“历史”。目前的历史课,不是在教西方史学观吗?不是在鼓吹落后就会挨打吗?落后凭什么就要挨打?大家的历史观,一直都是同生共荣,落后,只意味着你应该得到帮助,这才是人性。目前的历史课,到底在教哪种价值观?
什么决定体系?理念、结构和办法。材料反而是次要的。
大家的工作目的,应该是在中国教育体制中,重建当代的中华文化教育体系,使之与西方文化教育体系相并列,然后互相交流,互相融合,使学生既学到正宗的西方文化,又学到正宗的中华文化,并能出入比较,悠游其中,如此,才能培养出面对世界的革新型人才。
重建中华文化教育体系!
并非教中国传统的常识和技艺就叫国学教育,而是用中华文化精神做教育才叫国学教育。最后培养出来的,是有中华文化精神的学生,而不是用西方文化精神解析了一些中国传统常识的学生。
所以,大家第一要知道什么是中华文化精神,然后要明确中华文化精神应该配合有哪些样的教育理念、结构和办法。
探寻中国古时候教学真相
先看一幅画,宋朝的《圣迹二十四图》,这是描绘了孔子一生的二十四幅图,其中的一幅叫做《孔子授学图》,画的是孔子周游列国后回到鲁国,开门授徒,讲课的场景:
可以看到,在孔子的课堂上,至少是在宋人想象的孔子的课堂上,大多数学生都没认真听讲,而是各忙各的。孔子的身边倒是有两排人,可是没一个人的双眼是看着孔子的。——孔子只给一个学生上课。两边的学生是排队的。
知道中国古时候教育真相,让大家从这个惊人的真相开始:一对一教学。
从《论语》到民国文献,到大家亲自采录的上千位读过私塾的老先生,所有些证据都指向——个别教育。所有些中国古时候的老师,讲课的时候都是一对一的。当然有概论课,有讨论课,有活动课,这类是大伙在一块上的,但,真的的传道、授业时,是一对一的。所以古时候中国的教学效率天下第一。
当初民国搞教育改革,全盘西化,老师从坐着讲改为站着讲,从一对一改为一对众,出现了统一教程和统一考试,当时有不少老师离职。为何?由于教不了。不少传统教育的老师,面对一群学生,不会教。今天不少老师一对一不会教。历史常常就是这么开大家的玩笑。
可能有些老师会奇怪,面对一群学生上课有哪些不会教的呢?让大家回想一下上课的场景:
老师开门进教室——上课!
学生站起来——老师好!
老师——同学们好!请坐!今天,大家讲第五课……
打住!就在这里,请老师们扪心自问——你为何要上第五课?哪些原因?什么理由?
唯一的原因就是:昨天上完了第四课!
可是,有些学生第三课都没掌握,有些学生可能第九课都学会了,你却在这里上第五课,你能说说到底是给哪个上的吗?给具体哪位学生?到底是哪位学生需要上第五课?
老师怎么样决定进度?是根据学习好的学生,还是中等学生,还是差学生?无论如何决定,都是大部分学生被抛弃。这里不可能有教育公平。
大家的文化觉得,世界没永恒不变四海皆准的固定规律,只 有“道”。“道”只不过大致的方向,它是变化的。变的方法是“一阴一阳”。这类宝贵的思想对于人类来讲太要紧的,大家一直给人类提供着与西方不一样的思维和世界观。这类世界观和价值观假如不可以让学生最后理解,就不是中华文化的教育。
西方人觉得世界是有规律的,或者有上帝的,所以教育也是有规律的,所以统一教学、统一教程、统一考试、统一毕业。中国人由于觉得世界是整体的、变化的,所以人也都是不同的,所以大家是一对一教学,每一个学生的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进度和教学办法都不同。这个班有多少学生就有多少课程表。每一个人都不同。
这不止是个教学效率的问题,而是更深层、更要紧的世界观问题、价值观问题。
有位台湾的名师给初中生上课,讲“仁”。他没解说《论语》名句,也没分析“仁”的内涵,而是问学生们一个问题:假如跟朋友约会,他们迟到了,见面后你的第一句话会是什么?学生们回答什么的都有。于是他把回答分两类。一类是为他们着想的,一类是没为他们着想的。前者是面向“仁”的方向的,尽管还差非常远。后者则是背离“仁”的。于是学生们恍然大悟,课堂氛围活跃。观摩的老师们也都交口称赞。
我却不以为然。由于,每对情侣的状况都是不同的。非常难说第一句话如何说就是“仁”或者“不仁”。如此的分类,简单暴力,无视个人的处境,事实上教学态度本身就背离了“仁”。如何可能指望学生理解“仁”呢?
在《论语》里,大伙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给每一个人的回答都是不同的。为何?由于他是针对提问者的状况回答的。他了解对什么人、啥事应该如何不同地做,所以他才是了解整个“仁”的人,是得道之人。你想问个“仁”的统肯定义,孔子只能针对你的状况回答你该做的。你了解了整个的概念,对你有哪些用呢?有害无益。
大家看一幅日本的画吧,《菅茶山授学图》。
菅茶山是什么人?他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前的一位著名诗人和思想家。他的学生们参与发动了“明治维新”,所以他也是日本近代史上尤为重要的教育家,被列入“明治维新百杰”。
菅茶山上课,是在他家的院子里。他坐在宽大的屋檐下,学生们则团团围坐在院子里。他是一对一讲课,还是统一教学呢?
2014年我去日本采录吟诵时,顺便去了菅茶山的学校遗址,拍下了一组照片。
现场还真如画中所呈现,有宽大的木台和院子。可是,有一个奇怪的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走近一看,原来是两个石头盆子,一个高中一年级个矮,一个圆一个方,里面蓄满了水。
我当时问遗址的导游:这是什么?他回答说:这是菅茶山先生的洗手盆。他每次上课前必洗手。
我开始想,日本人就是讲究卫生!上课前还要洗手。但转念一想,不对呀,有哪个洗手需要两个洗手盆的?于是我又问导游:为何有两个洗手盆?导游回答:哦,是如此,菅茶山先生觉得,大道如水,在不一样的容器里会是不一样的样子。所以菅茶山先生筹备了两个洗手盆,他每次上课前都要洗手,提醒自己,大道在每一个学生的身上都是不同的,不能统一地教他们!这是他的座右铭。
让大家看看大家我们的古时候教育吧。
这是清末学馆的照片。大家可以了解地看到,老师是一对一教学的。旁边站着排队的学生。其他的学生各忙各的。所有都跟《孔子授学图》是一样的。
不过,这张照片里有一个奇怪的地方,你看出来了吗?
就是老师坐的地方。老师是坐在学生们的后方,在教室的角落里。在《孔子授学图》里,孔子也是坐在教室的角落里。
今天大家的老师也会坐在教室后面的角落里,但那是班主任监视学生。上课的时候,老师是要站在讲台前的。
可是古时候的老师讲课,是在教室后面的角落里。甚至是在另外一间屋子里。回想一下孙奥创是如何学的七十二变?慧能是如何传的木棉袈裟?这是为何呢?
亲身去感受一下就会了解了:不同在于私密性!
中国古时候的个别教育,包括两个条件:一对一,和私密性。
中国古时候的儒家教育大体分为两支。一支是程朱,一支是陆王。程朱这支的教学大纲首推朱熹的《小学》。大家去韩国采录,发现韩国的儒学馆至今还是需要学生全文通背《小学》,包含注解。这是古时候儒家教育的课标。目前风行的《弟子规》,也是从《小学》的一些话里化出来的。陆王这一支的教学大纲,首推王守仁的《社学教条》。《社学教条》和《小学》不同,它不是普通的学术著作,而是阳明先生做南赣巡抚时颁布的政令。内容包含教育理念、教学办法、课程体系和课程表。大家看看明朝的公立学校,天天的第一节课是什么内容:
每天清晨,诸生参揖毕,教读以次偏询诸生:在家所以爱亲敬长之心,得无懈忽未能真切否?温清定省之仪,得无亏缺未能实践否?往来街衢步趋礼节,得无放浪未能谨饬否?一应言行心术,得无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笃敬否?诸童子务要各以实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教读复随时就事,曲加诲谕开发,然后各退就席肄业。
第一节课,是老师跟学生一对一地谈话,谈话的内容是:从昨天离开学校开始,至今回到学校为止,出了什么事?有哪些喜怒哀乐、哀愁烦恼,都告诉老师。
这才叫做“立德树人”的教育!常识和技艺不是目的,生活态度才是归宿。《社学教条》开篇即说:
古之教者,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词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
由于教育关注的是心灵,所以需要老师和学生之间要互相知道、互相信赖、互相喜欢。如此才能“传道”,即把我们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传给学生。假如学生和老师之间互相不知道、不信赖,那样只能传常识和技艺,是传不了“道”的。目前大家的老师上完课就走人,不少学生直到大学毕业,也没跟老师单独谈过话,除非是被叫到办公室挨批。
古人云:1日为师,终身为父。大家都以为这是夸张,或者等级压迫。不了解这是古人对于老师的需要。老师总是要比爸爸妈妈更知道孩子。如此才能做教育。
想一想,世界上所有些心灵教育,都是私密进行的。基督教有集体布道,也有忏悔室。忏悔室甚至需要师生之间互相不可以见面,不可以知道他们的身份。今天的心理学教育,也是要一对一私密谈话的。
假如确认国学教育的目的不是常识和技艺,而是理想和信仰,是“立德树人”,那样一对一的私密谈话就是需要要做的事情。
学校内的传统文化教育怎么样拓展?
老子云: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至于无为。
若是学习常识和技艺,那是没止境的,会越学越多。但假如学习的是“道”,是生活态度,是世界观,那就没那样难。只须记得,学生背不背得过经典、是否会吟诵、书法怎么样等等,不是非常重要的,而是透过这类渠道,培养他的生活态度、品德修养,那就好办了。大家无需追求内容的多寡、层次的高低,大家只须求学生知道中华文化精神到底是什么,跟西方文化有哪些不同,价值在哪儿,并熏陶他的品性,可以改变他的生活态度。
如此的一个教育过程,不可以期待学生自己完成。要了解学生生活在2016年的现代社会里。古圣先贤没直接说过在这种社会里该怎么样生活。讲一句大道理,学生就了解怎么样处置身边发生的事吗?这连大家成年人也非常难做到,还能指望学生做到吗?
假如学生办不到,所有教的常识、技艺和大道理,就成为空谈,成为应试的负担,而反过来对心灵教育没益处,由于如此的教育本身就是漠视个体、漠视心灵、漠视生活的!
用漠视人性的态度教国学,还能指望学生亲近国学、理解国学、传承国学吗?
于是剩下的就只有为考试而学,为升学而学,为好工作而学,还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经史子集,培养的是伪君子。那不就是作孽吗?
自明末以来,国学教育首次面临这么好的复习局面,这是全民族长期的探索的结果!但假如由于大家的失误,第三陷进假道学的泥潭,那就不止是对学生作孽了,而是对中华文化作孽。一旦失去民意,中华文化的前景堪忧。
怎么办?
答案就在看上去不可能,但其实非常简单的一个做法里:
个别教育,私密谈话,关爱心灵,伴随成长。
(节选自:国学生。本文也是徐健顺先生在江西第一届出色传统文化教育高峰平台上的讲演稿)
扫描上方微信二维码,关注阳光家教网